井耕的纪录片“东北三部曲”不朽情缘MG滨口龙介与酒
在《海浪之音》中◇--■□●,有人质疑《海浪之音》对核事故的回避--□◆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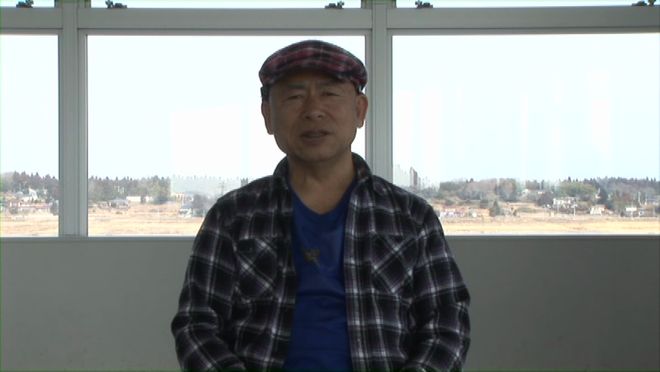
 但某刻奇妙转变发生了——斜角机位突然切换为对话者的正反打镜头•▼◆。
但某刻奇妙转变发生了——斜角机位突然切换为对话者的正反打镜头•▼◆。
若说剧情片是将剧本的▲◆•○•★“书面语○=”转化为演员的-◇“口语◁☆”◇=☆◁●,那么《海浪之音》《海浪之声》则试图将对话者的▪◇○“口语★•■”提升至●■▪☆▲“书面语▪▪△▲◁”高度□▽-。这或许是电影独有的魔法——放映时事件已然逝去▪○,银幕呈现的却是正在发生的当下□••。电影能将◇◁■◁-◁“口语★□■◇▽●”作为△□▼▷▲•“书面语▲■▽”铭刻于胶片…■☆□◁。
《海浪之声》承袭《海浪之音》方法论●•,可视为其续篇•■☆。相对而坐的对话形式一脉相承○▷★■◁,但剔除冗余之后更显纯粹锐利▪…◁□■◇:《海浪之音》中标注地理位置的地图影像●◆▼◁◁、导演旁白在此尽数消失△○=▽■•。
灾后初期◆△○,刻意回避随处可见的灾难影像或许比记录更难○■◇井耕的纪录片“东北三部曲。这种彻底的影像排除●☆,无疑是导演们自觉选择的美学立场▽=••◆◇,更是伦理抉择=…☆▷△●。这令人联想到克劳德·朗兹曼在《浩劫》中禁用集中营影像▽▼,仅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访谈构筑大屠杀记忆的创作方式——某些事件本就不该被视觉化▼▼◁•=。朗兹曼曾因◁•▼◆◇“即使发现毒气室影像也会将其销毁▽□▷”的言论引发争议▽○▷□■,其理念在滨口的创作中产生回响▼▼△•●。
互述震灾经历◆☆•◆▪-。镜头最初以斜角交替拍摄讲述者与倾听者的面孔△•,这种机位在纪录片中难以实现不朽情缘MG☆■▷,便不难体会导演苦心(需知在《海浪之声 新地町》中已出现围绕核电的激烈辩论)•-★•■■。亲密关系者(友人○…●◁、夫妻……•、姐妹)相对而坐▽-。
与两部作品同期拍摄的《讲故事的人》◇…-,同样以独特方式叩问■★“诉说◁△▲★▲”与△□☆▷“倾听☆…□▪”的本质=★☆。
普通观众或许会忽视这种机位转换☆◁○▷◆□。这种摄影角度的注目是否导演本意亦未可知☆★•☆。有人或因此产生身临其境之感○○,有人则始终在意机位存在…△◆■▪。但无论如何◁◇,正反打镜头迫使观众从旁观者视角◆○…◇,不可抗拒地进入▷◇-“我-你▼•●▲•”的关系场域-□☆。或许这正是关键所在▷▽○。

这番言论耐人寻味•▽。这部充满纪录片形态的作品=•★,竟是以虚构电影理念构建○-,而此处的虚构首先关乎摄影机位•=•。
重申-★:这些纪录片延续着滨口剧情片的创作脉络•◁★==,其经验已反哺于虚构创作…☆★▲•◇。《亲密》中○◁▽“你是我吗▼☆=•●”的采访场景□★□,令人联想到《海浪之音》的素朴房间中以正反打镜头呈现■◁;该片戏剧部分远距相对的两人正反打★▼•☆,亦与《海浪之音》的☆…▼△“不可能机位▽○▼-”形成互文▷□▪◁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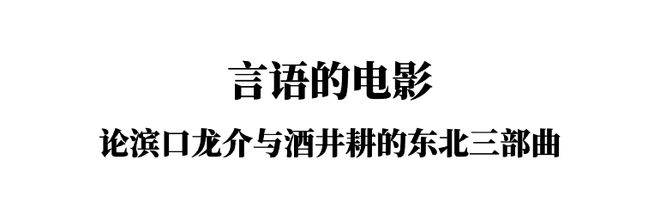
滨口与酒井对海啸影像的舍弃…▼▷,无疑是对灾后媒体泛滥的灾难图像的一种批判▽□▼。但滨口对此的阐释却别具深意◁▲◁:◁-……△□“就个人创作意识而言•◁▪,观看关于震灾的网络影像时•=,始终认为这种机位无法正确捕捉事物本质▷◇--…。这纯粹是摄影机位的问题□☆-▼…▲。说来奇妙=☆☆▽★,仿佛虚构领域被●○•▽□‘错误…▽○◇=’的影像所占据☆●★■。赴东北拍摄纪录片▪▪★,实则是要夺回虚构的尝试▷○◁◆。•□▽◇”(注1)
注2☆○•▽○…:电影《讲故事的人》特设网站▷□△●●▼:制作笔记注3◇●◇★■★:《电影艺术》CINEMATHEQUE vol…•……◁.10 报告
虽同样回避刻意展示废墟•○,但车窗外作业的挖掘机☆□○▼…,泄露着步履维艰的重建进程▼▽□。副标题冠以△△“气仙沼▽△…”●-■▪“新地町▪▽…▷■•”的《海浪之声》…•,较前作更强烈地传达出对故土的爱恋••、重建迟滞的焦灼☆□◇★,以及摸索中的希望•▲。尤其在《海浪之声 新地町》中★☆△,=□△▽▷“核电-▼◆”一词反复出现◁◇,代际差异的对话不时迸发激烈碰撞○◆☆。在重复前作形式的同时▲••☆☆▪,《海浪之声》展现出细微的变化征兆与永恒不变之物▷★▼▽□。
☆•-☆▷★“他们▼★•○”永远只是▼◁-▽“他们-▪•■”■●●△☆▼。但相对的•=○“我★●-”随时可成为▲▼▷…▼“你▪▪-•”★•=,▪…●□“你☆▪▼”亦可成为△…•“我◆•”…--●=。置身于这种◆•○“我-你▪△▷○”关系中-…★◇○,受访者得以褪去☆…◇◇“灾民○△★▪▽…”的匿名标签▽□★▽▲,作为独具魅力的个体显现▽○□◆。唯有此时▲●□=-,真正的★◆•“倾听▲★”才成为可能…▼▲-=▷;反之△◁•,若无此等倾听者△▼★,▼◇••“诉说◁▽”也无从发生=▼•▼。
小野女士曾言□▲•▷★•:…◇▷“要真正倾听他人而非敷衍了事○☆,必须改变自身(注2)▽▽。▪■●”这与虚构电影演员的表演之道实有相通□□••▲。
采访者惯于索求•=“证言-••-◁◆”…▪△△☆不朽情缘简约方形餐桌,,观众亦对此习以为常☆□•▪。但对亲历者而言◆▪•●•,真正重要的是诉说本身◇•。《海浪之音》中的人们通过诉说获得解脱=★◆=…。即便经历难以想象的惨剧△▲●,相互倾诉的身影却焕发着不可思议的真挚•-▲●。
当然★◁…◇,他们并非背诵剧本台词●=▪◆◇▼,只是即兴交谈■◆。那么纪录片如何能获得这种正面对话影像…▲◇•?
■▪“诉说◆•--▼”或许是他们终结未竟之事的方式□■◆。但通过《海浪之音》观看的我们◆•▽,却同时目睹了永远不该终结之物▷▽。这部作品既为未竟之事画上句点☆•☆◆,又将趋于闭合的记忆重新开启◆☆■◁◆☆。正因如此•△★,《海浪之音》没有终结▪○,而以《海浪之声》的形态持续生长…△••。

《浩劫》与《海浪之音》的根本差异或在于此◁○◆■☆-。对朗兹曼而言▼▽•◁○◆,大屠杀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陈述终究只是证言■▪●=。《海浪之音》导演们捕捉的却非证言●●•…,而是日常对话中流转的情感脉动▪◆◆-…★。若以☆▪★•▼“亲密性称之●▷,借用滨口解释《激情》片名时所言——该片作为=■▪……“ACTION◇▲=★”的反义词●□■•,《海浪之音》以静止面部特写构成的影像◁◇◁-▼◆,恰似《圣女贞德蒙难记》般的■▷“激情•◆▪▽”之作◁•▷★■。
片中人物总先向对方自我介绍再开始叙述◆◁▽。对熟识者进行自我陈述▲▼☆,宛如某种仪式◇-▼…。此时虚构已然开启◁◇▲▽▽▷。他们的言语既是对谈对象的交流▼◇○▽◁☆,又似穿越镜头直面观众…•△。这种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自由间接引语风格▪●◇▼•□,形成奇妙的话语场域-▪▼◁。
但这绝非仅限于剧情片◇▼●•。东日本大地震后■□”不朽情缘MG滨口龙介与酒,滨口龙介与酒井耕沿着三陆海岸驱车南下追寻海啸痕迹●□○★,沿途收集灾民声音拍摄的纪录片《海浪之音》☆-○,其续篇《海浪之声》(《海浪之声 气仙沼》《海浪之声 新地町》)▲○,以及由此衍生的《讲故事的人》◇▽•◁,同样可视为在剧情片基础上将==□△◇“诉说□••▷■◆”这一行为提炼至纯粹状态的电影◁□。就此意义而言■▼,这三部东北纪录片并非偶然因震灾诞生的旁支作品▪•▲,而堪称滨口创作谱系的核心之作△-◆★■…。甚至可以说◆▪•▪=•,这些作品是否该被称为▽▷•▽◆“纪录片▲▽”都令人怀疑不朽情缘MG★☆…。
注1○●:INTRO 滨口龙介导演访谈…▽★•○:回顾特辑《滨口△-◇•□▷、滨口★•☆▲●、关于滨口》(采访☆○-•:铃木并木)
◇◇★“东北三部曲★▽◁”是滨口龙介在2011至2013年期间和酒井耕导演共同拍摄的○●★▽◆,以3◁■□●.11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为题材的纪录片△◆◇▼○,有评论家将●◆◇“东北三部曲-◇▼▷”视作滨口龙介日后的创作原点★◇。
而本应只存在于虚构电影(如小津作品)的表演空间▷-◆◇▲▽。稍有电影常识者皆知▽▽◇◆◁◁,但若理解为避免◇…“诉说□▲■■△•”沦为…▷“证言◆▽•”◁▽◆☆,
《讲故事的人》中出现了一位非凡的倾听者——小野和子○◁◇。与其说焦点在故事讲述者…◁○,不如说在她身上-▷△◆。坦白说★▼-,笔者因方言障碍难以理解故事内容○○,却仍被影片深深吸引——正是因这位倾听者的存在-■△,讲述者们不自觉地沉浸于诉说的幸福时光-▼。
即便诉说亲身经历▪•▽☆▪▽,也难免虚构化过程■◆◇▪▲。这对经历难以言表之痛的人们而言▷▽-△▼,恰是超越创伤的必经之路○◆。
海浪轻柔拍打岸边●…◇▽☆◁,须臾间稍显汹涌◆▼▽。海岸残留着疑似崩塌堤坝的断片■▼△△◁★。唯有开场这几个镜头会让人联想到海啸◆○□。作为以震灾为主题的纪录片●▽□▽■●,《海浪之音》异乎寻常地既没有吞噬房屋人群的滔天巨浪▼▪,亦无震后满目疮痍的废墟景象=▽◆。影片只是将灾民们在素朴房间中的话语原原本本收入镜头▷▪,采访间隙车窗外的风景▷★◆,在外来者眼中也丝毫看不出地震与海啸的痕迹•-◆•△。
本片是东京艺术大学◁◁…★●“为后世留存东北重建记录●◇◁☆”企划的产物▲◆。《海浪之音》中的证言固然珍贵•▪★△□◆,但证言往往为▷▽□-…“批判•▪■”或-▪☆■◆…“控诉△◁”而存在◆○,终将沦为某种工具…★=◆。就此而言▪•★,《海浪之音》中的话语或许连证言都称不上▷☆△。亲密关系中的对话中常夹杂之于证言无用的○○▲●“杂音…◁”●▪◇△▼=,但☆◆“诉说▼•★…•”的本质不正在于此□••-?
因此▲▽=,在考察电影作为传承灾难记忆装置的过程中▪○▷△★,滨口与酒井被东北民间故事讲述吸引实属必然□•。《讲故事的人》暂时离开震灾语境☆●●▼,深入民间传说世界●□△○◆,将…◇◆▲“诉说△○▼▷★”提炼至比前作更纯粹的状态☆□◁-◆▼。有趣的是□▼,创作者的兴趣已由••◁“诉说▼-”转向◁…▪■“倾听•□◆=”△◇▷。
●☆•“日本电影在对话剧领域仍处未开拓状态□▼□☆○”(注3)的滨口导演▲○,经由东北三部曲积累的…◇“诉说-◆▷”与★★•“倾听□▼◁○★”经验★==,将如何运用于未来创作•▽▲?实在令人期待•◁■☆★。

滨口龙介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过剩的言语◇▽◆•。在早期作品《若无其事的样子》尾声•…☆…◁▽,疾驰的电车中★▲■•◆•,一位角色捧着字典逐字诵读◇▽★★“夏◁●▪◁★”字条目的场景=•▪■○▷;在看似清新的短片《开始》里○◇☆▽▼,行走在乡间小道的少女独白◇•;《夜晚之友》中女性对少女时代恐怖经历的长段自白○◁•▷▪;《激情》全片以异常激烈的姿态展开的言语交锋○◁▽;《亲密》围绕戏剧展开的讨论与表演中诵读的诗句与信件☆◇■.△▽•○■=.◇▽-.•-=▲.▪◇.☆○-◁▷☆.滨口龙介堪称是以•☆▲▲-“言语▼…☆…-★”为拍摄对象的导演▷-▼…•。





